涉猎广泛为文学界全才
潍坊晚报 2023-01-08 10:03:18
黄裳在来燕榭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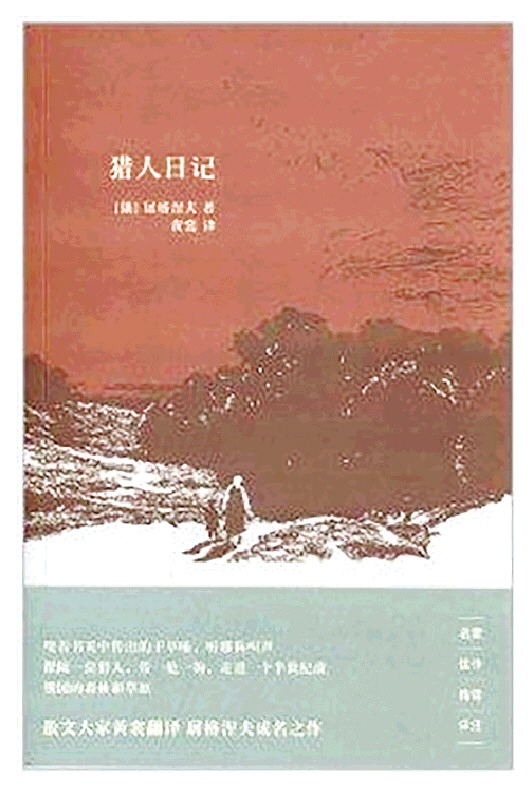
黄裳所译《猎人日记》
黄裳2002年11月题赠。
黄裳是多面手。他既是作家,又是记者、藏书家、翻译家,涉猎戏剧、新闻、出版等多个领域,在当今文学界,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全才。在所有“标签”中,他最看重自己的“散文家”身份。而他的游记写得堪称“独具一格,不可复制”,其杂文则以直言不讳、辛辣尖锐闻名。
早期任职《文汇报》 散文笔法写通讯
1946年7月,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,担任《文汇报》记者,同年8月成为《文汇报》驻南京特派员,《旅京随笔》正是受编辑委托撰写而成。这组文章重在写从日本践踏之下获得重生的南京的“文化情形”,其中最为著名的是《老虎桥边看“知堂”》。这篇以散文笔法写成的新闻通讯,其实并不只是“看”周作人,而是访谈周作人,剖析周作人,批判周作人。对于周作人的题画诗:“墨梅画出凭人看,笔下神情费估量。恰似乌台诗狱里,东坡风貌不寻常。”黄裳一眼就看出周的“愈益丑恶”,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坟旁的秦桧,历史要他永远地跪在那儿,“白铁无辜铸佞臣”,大节有亏,便无足观。那般光景,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。还有《更谈周作人》,对周作人“大谈其以第三流文化人保存沦陷区的文化”,痛加批判,斥之为“简直使人肌肤起粟”。
黄裳还参加过周恩来在梅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,对周恩来印象极为深刻:“周先生回答问题的才能是极可钦佩的。无论正面反面侧面,尖锐的,笼统的,或甚至有些锋芒透露得使人难以回答的问题,他回答起来都不成问题,而且往往都是妙趣横生的。有时离开了对原题的注意力,神往于他的词锋的所及。”
翻译世界文学名著 摆脱食洋不化通病
黄裳是翻译家。理工科出身的黄裳精通英语与机械,在抗战期间,因给来华美军任翻译,曾翻译驾驶坦克的说明书,供训练使用。这也是黄裳与翻译结缘之始。
黄裳最早的译作是一本数学读物《数学与你》。黄裳在《关于开明书店的回忆》中提到《数学与你》时说:“它带着你渐走渐高,绝不吃力,最后终于看到近代数学与哲学艺术的瑰奇无限的景色。作者是哲学家、诗人、艺术家,有许多幅作者手绘的插图给本书添上双重的美丽。”
而黄裳翻译最多的则是世界文学名著。在这方面,他深受恩师李尧林的栽培与影响。李尧林是黄裳在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、巴金的三哥。任教之余,李尧林埋头文学翻译。抗战后期,李尧林因病去世,所译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的《莫洛博士岛》,只完成了一小部分。抗战胜利后,黄裳受巴金委托,续译了小说的第9章至第22章。
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,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的现实,在他那个时代颇具话题和热度,受到很多人的认可,在文坛上有着极高的地位。黄裳翻译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平凡的故事》。
萨尔蒂科夫·谢德林是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,曾一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起称霸俄国文坛。黄裳翻译了其代表作《哥略夫里奥夫家族》,以流畅的文笔,译述风物景色,如诗如画;以灵动的文字,译人物话语,如响如唱,堪称经典。
《猎人日记》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。黄裳翻译时,一脱当时不少翻译作品“食洋不化”的通病,做到既符合原文的叙述习惯和句式结构,又不失汉语表达特点。像一首首抒情歌曲在读者面前缓缓流淌出来,汇成一部色彩斑斓、动人心魄的交响诗。
游记独具一格 杂文辛辣尖锐
黄裳是散文家。读黄裳的游记,其最大的特色,是运用其丰富的史地知识和优美文笔,把山川、历史、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。几乎每一篇文章,都是现实纪游和历史典故交织起来,两相贯通,彼此映衬,又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与独到见解,使读者获得启迪,引起共鸣。
他的文字,格调高雅,耐人寻味,如行云流水,挥洒自如,看似信手拈来,平和随意,实则熔知识、趣味、历史、版本于一炉,无不显示其匠心独运和高超的技巧,蕴含着极高的思想文化价值。独具一格,不可复制。这样的文章,是风景中的历史,又是历史中的风景。正如他自己所言,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,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,也将是没有生命的。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,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片那样的东西,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。
看画时爱读题跋,游园时留心匾对。面对湖山,也总是时时记起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。黄裳正是这样“思想指挥着材料”,以学人兼才人的厚重文史积累、深邃的识见、开阔的视野、丰富的联想,凸显出其学者散文的历史性和思考性特征。著名作家孙郁评价说:“读之如清风明月,林中甘泉,良多趣味。”
黄裳又是著名杂文家。杂文在黄裳的文学作品中,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虽因杂文而多次惹祸上身,但他始终不改其志,依然敢说敢为。
1950年4月4日,黄裳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一则短文《杂文复兴》,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,遭到了“大量的驳斥”和“声势浩大的批判”。事实上,自1950年以后,黄裳一直“惹”麻烦,幸亏有巴金保护他。
到了1957年“反右”,黄裳终难逃一劫。因为一篇题为《解冻》的报道,黄裳被打成“右派”。“文革”时被下放到印刷厂当搬运工,那时他的朋友郑重经常见到他:“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,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,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,操作自如。他身体敦壮厚实,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,就像一座钟,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,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,心中也感叹着:‘真是一个人物!’”


